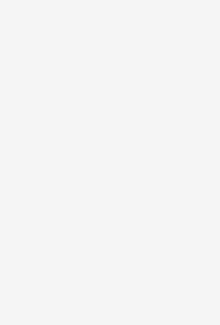我在麻理体内 已完结
分类:日韩剧 地区:日本年份:2017
主演:池田依来沙,吉泽亮,中村由利佳
导演:スミス,横尾初喜,戸塚寛人
更新:2022-10-09 09:17
简介:本剧改编自大志三三的人气漫画。小森勋(吉泽亮饰)是一个整天..本剧改编自大志三三的人气漫画。小森勋(吉泽亮饰)是一个整天玩游戏和自慰的年轻人,一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一直跟随他的高中女生吉崎麻里(池田饰)。 ,柿口由里(中村由里香饰),发现内容不一样的同学,试图找出真相。 福柯用知识型(épistémè)来描述真理得以生成的前提。那么,如果主体将自己所经历的经验事实视作真实的,这一主体本身,作为其经验的前提,或许也可以被称作一种知识型。在主体重塑身份的过程中被重塑的,正是这一知识型。这一过程必须是暴力的、创伤式的。或许可以称之为:认识论断裂。 齐泽克在某次论坛中曾经谈到酷儿理论和跨性别群体当中一种内在的对抗性。对于朱迪斯·巴特勒等等酷儿理论家而言,性别并非生理决定,而是由历史、社会通过表演性的、话语性的实践建构的产物。简单来说,性别的形成在于我们要求女孩像女孩一样举止,要求男孩像男孩一样举止的过程中。然而齐泽克却注意到,在进行变性手术的跨性别者当中,许多人却使用着一种与上述历史建构主义恰恰相反的语言:“我很感激,我现在终于可以在我本应出生于的身体中生活了。”这种本质主义的话语似乎意味着在出生之前,性别已经写入了这些跨性别者的“灵魂”当中,而他们出生于他们的身体当中完全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错误。 这不是说朱迪斯·巴特勒们错了,也不是说跨性别者们不应该这样理解自己。齐泽克强调的是,在今天的性别理论中,对于性别身份的理解倾向于想象一些精力充沛、自由浮动的身份,似乎它们可以任君采撷;而性别理论家们所忽视的是,在作出身份变换这一激进决定的过程中,一个人所需要经历的那种痛苦与创伤。最高程度的自由行为,在齐泽克看来,恰恰是以必要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眼前,而非那些通常意义上的自由选择。当一个人选择为国捐躯的时候,他认为自己不得不为国捐躯,如果不这么做,就是背叛了自己。这不是说他不自由,而是这种激进的自由选择必须被主体经历为必要性。恰恰是在经历这种必要性的同时,我们自由地决定了我们自身。而对于性别身份的自由选择,同样地,也必须被理解为某种必要。(顺手把这个视频翻译了一下扔到了B站)齐泽克论性别身份和跨性别主义 | 这种创伤性的、痛苦的体验,这种不得不成为自我的必要性,在我看来,正是《我在麻理体内》这个故事的关键所在。(下文剧透) 《我在麻理体内》从头到尾就像是押见修造向宅男们开的一个玩笑:宅男一夜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JK美少女;而真相却恰恰是这一俗套幻想的反转,JK美少女一夜醒来把自己变成了宅男。无论这个玩笑开得有多么离谱,不得不承认的是,押见修造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理由来合理化这一翻转。 吉崎麻理作为学校里受欢迎的美少女,是许多人憧憬的对象。每个人都对她怀有憧憬,这恰恰是麻理的厄运。当桃香、桃香男友、麻理母亲无不将自己的欲望强加于麻理身上时,麻理的形象就由这一系列他人的愿望投射而成。麻理,成为了最受注视,却最不受注视的个体。其存在仅仅是为了回应所有人的期望。当麻理变成宅男小森功时,由于她无法完成这一系列的回应,便必须承受桃香的排挤、母亲的埋怨。麻理作为一个主体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回应他人的这些“唤问”。对于这种唤问的抵触同时也阻止了麻理以同样的方式唤问他人。正如柿口依清楚地注意到,麻理从来不说「可愛い」。这正是因为麻理的母亲认为“麻理”是个「可愛い」的名字,因而一意孤行地把女儿的名字从“文子”改为“麻理”。麻理无法说出「可愛い」,正如她无法接受自己被叫做“麻理”。呼唤名字这一件日常生活中最寻常不过的事情,在这里却突显出了一种义务——按照人际关系对他人作出回应的义务。 而名字蕴含的这种义务,在《我在麻理体内》中,也被放大到极致。麻理经历了两次改名:第一次,由奶奶起的名字“文子”,改为母亲起的名字“麻理”;第二次,由母亲起的名字“麻理”,改为通过复制小森功的人格而得来的名字“小森功”。在这种变换过程中,名字与人之间看似自然的联系被彻底撕碎。当“文子”被改名为“麻理”时,即意味着麻理与奶奶的亲密关系被切断,麻理臣服于母亲的欲望。而当麻理通过人格变换将自己变成“小森功”时,亦即摆脱了与(几乎)一切他人欲望的关联。通过“小森功”对“麻理”的憧憬,麻理不仅将他人的欲望切断,更将自己的欲望重新导向了自身,以自恋为自己提供了绝对拥有的自我关系(ep3的自慰情节)。 需要注意的是,当麻理将自己变换为“小森功”时,有一关键的差异,使得这一“小森功”的人格与真正的宅男小森功处于完全不同的状态:“小森功”对“麻理”的欲望。真实的宅男小森功并不知道麻理的存在,他的一切欲望都以最简单的形式解决。然而在麻理所产生的“小森功”人格那里,“麻理”不仅存在,更是“小森功”的世界里唯一值得憧憬的圣少女。这种神圣的地位甚至使得“小森功”一度不敢触碰自己的身体。只有在发现宅男小森功并没有与自己人格互换,也就是确认了“麻理”的彻底消失时,“小森功”才有胆量触摸自己的身体,想象“麻理”和自己融为一体。麻理体内人格之间的这种复杂的依恋关系反过来固化了“麻理”人格的形象:“麻理”必须是无意志的客体,他人欲望的投射产物,哪怕是新的人格“小森功”也必须以这种方式想象“麻理”。通过人格分裂,麻理成为了自己欲望的主体(“小森功”)和客体(“麻理”),从而使得自己能够不受限制地保持自恋状态,其代价是"麻理"的永远缺位。(宅男醒醒吧,美少女渴望成为的不是彻头彻尾的宅男,只是拥有宅男特质的美少女而已。) 诚然,摆脱一切他人投射的欲望,正是麻理憧憬成为小森功的原因。押见修造确实是在和宅男们讲一个自嘲的内行笑话:没有人会对废宅有欲望。恰恰因此,废宅是渴望逃离复杂人际关系的美少女JK的最佳选择。而成为小森功,并非简单的选择即可做到的事情。正是那一切束缚住麻理的社会关系,在它们对麻理的唤问当中,构成了作为主体的“麻理”。在试图摆脱这一切关系的同时,麻理面临的是一场主体的危机。如果“麻理”不复存在,那么这个拥有麻理身体的人又是谁?谁可以摆脱一切他人的欲望?只有小森。事实上,必须是小森。正是这种必要性,带来了麻理的人格变换。“麻理”将在摆脱他人欲望的同时消失,只有新的主体对她进行替换,才能够避免一场由主体消失引发的精神崩溃。 如果仅仅是这样的一场人格变换,结果大概也就是麻理被当作精神病,被送入医院。在其他人眼里,麻理仅仅是麻理而已,哪怕变了性格,只要照旧回应他们的欲望,那就是麻理;如果不能回应,那就是说麻理应当被他们以怨恨、愤怒来惩罚,直到她重新回应。真正拯救这一切的显然是柿口依。柿口并非对麻理没有欲望,然而柿口是唯一一个能够“认出”麻理的人。或者说,只有柿口认出了“麻理”的消失,以及取而代之的小森功人格。不仅如此,通过柿口对“麻理”的欲望,以及“小森功”对柿口的欲望,“小森功”对“麻理”的绝对自恋关系被打破,构成了“麻理”→“小森功”→柿口→“麻理”的三角欲望关系。在萨特的剧本《禁闭》当中,这种三角欲望关系带来了无人可以逃脱的结论:“他人即地狱”。在《我在麻理体内》这种三角关系却被巧妙推翻:因为“麻理”和“小森功”仅仅是一个人的两种人格,通过两种人格的融合,麻理和柿口成功地抵达了相互承认的友谊,使得两人从各自的禁闭关系中解脱出来。 以这样的分析收尾显然是不充分的,而《我在麻理体内》以“这样就足够了”达成的和解收尾在我眼中也并不充分。曾对麻理构成压迫的结构在最后一集当中神奇地缺位了。当柿口从麻理的房间出来,看到麻理在厨房为她准备早餐,没有任何麻理的家人在场。这只能被视作是不可思议的妄想。“这样就足够了”或许是押见修造/本剧的主创们自我安慰的话。当心理结构被呈现为不断反转的迷宫,揭秘这一心理结构的剧情固然能在一种悬念当中推进;然而对于麻理来说,要真正从压迫性的社会关系中维持正常的精神状态,除了发觉自我以外,显然也需要想办法与他人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本剧对于这一部分实在着墨不多。但或许,“这样就足够了”。如果有时间的话,这份分析还有许多值得拓展的方面。但可以肯定的是,就像柿口与麻理在欲望和理解之间的艰难探索一样,即使他人可能成为彼此的地狱,除了他人,我们也没有可以从地狱中逃脱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