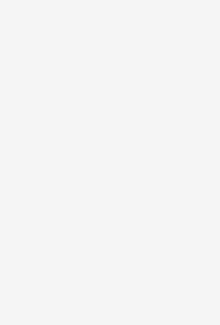盲国萨满 HD
分类:纪录片 地区:其它年份:1981
主演:内详
导演:迈克尔·奥普茨
更新:2022-10-10 09:49
简介:《盲国萨满》是一部神话史诗纪录片,讲述了尼泊尔西北部偏远地..《盲国萨满》是一部神话史诗纪录片,讲述了尼泊尔西北部偏远地区的宗教治疗。为了记录当地宗教习俗的基本特征,影片拍摄了18个多月。在宗教精神方面,这一特征在北亚的西伯利亚地区和广阔的喜马拉雅地区都有,并与大内亚地区的各种形式的萨满教传统相互联系,仿佛有一条线贯穿其中。 缘起 1970年代,米歇尔 ・欧匹兹在尼泊尔做佛教研究,意外路过鲁库姆区马嘉人村庄,一个当地男人问他:“你渴了吧?要不要到我家来喝水?十分钟。”这个无意中的邀约改变了欧匹兹日后的研究计划,他在那里一待便是两年。 前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只带了纸和笔,作为当地社会中一位沉默的观察者和参与者。而后,他想到影像记录会比书面记录更为完善,从1978到1979年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和同事们分三次进入村子,每次三个月,一共拍摄了35小时的16毫米彩色负片素材。 全部摄影素材围绕着萨满——当地宗教仪式的掌管者——展开。说到萨满的定义,早年欧洲学者在西伯利亚与中国东北地区做研究时,听见巫被称作“萨满”。一度,全世界多种文化中的巫师身份都被称作是“萨满”,它们被认为是萨满文化的变异。 而欧匹兹却认为,有多少萨满社会与文化就有多少萨满教,一些地域相近的萨满文化之间存在相似性,甚至地理上相隔甚远的文化也可能彼此呼应,与其清晰界定萨满一词所代表的意义,不如深入对特定萨满文化做观察研究,深入比较细节,再得出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是否相像、有什么样的传承关系的结论。由于这样的意图,我们就看到了纪录片中对当地社会宗教仪式、农业生产和社群关系的生动呈现。 整部纪录片分两部,时长总共三个半小时,全片没有一以贯之的情节线,而是由一个接一个的仪式组成,乱哄哄的唱诵、聚散和装饰从始到终,萨满的一举一动都旨在平衡人鬼之间的关系,从而治愈当地人的病患或者烦扰。 大主题在于展示在这个独特族群中,萨满与现象间的互动关系,他在这一社群中的功能是什么。全片由二十多个主题块组成,包括打猎、捕鱼、农耕、田园牧歌、家庭活动、以货易货、丧葬仪式、集体劳作,还有萨满教的诸多主题,包括唱神话歌曲,多种治疗手段,仪式前和仪式中、敲鼓和其他随身器物、预言未来和死亡。这些主题块彼此交织,相互联系。 有意思的是,欧匹兹在观察马嘉人看纪录片的反应时,发现他们最喜欢最着迷的是最平淡无奇的日常琐事,比如煮玉米。“我觉得原因在于,萨满活动本身就有表演的性质,最简单的事情一定是最伟大的奥秘。”当他们身处于萨满活动当中之时,他们本就是观众;而从农业劳动者的身份跳脱出来,观看这些日常行为,司空见惯的场景却成为了饶有趣味的景观。 文明的真相 在不免好奇心作祟的追随中,我时常为砍活羊头和鸡头供萨满吮吸的血腥画面而感到惊异,为渔网笼罩村民以给予庇护而感到滑稽好笑,而除此之外,纪录片所记述的萨满文化并未跳出我心中早已建立起来的关于“落后”文明的“刻板印象”。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以列维・斯特劳斯为首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揭示了亚马逊原始部落文明的样貌,构建了关于“落后”文明的一般范式。在看得见的世界,人和世界的关系寄托于他们与社群、与土地之间的关系,繁衍生息的日常也由此而建立;而在看不见的世界,人和鬼神的关系、人如何处理死后的世界,同样决定了部落的活动和空间布局。 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也由此而浮出水面:为什么生存越是依附于土地,就越是“迷信”?看不见的世界是随着实证思辨而应当灭绝的空间,还是随着农耕文化失落的一层真相?我无法回答,正如我也无法回答,结构人类学家所构建的范式是否可以套用到一切“落后”文明之上,文明以其本身而自证其成立,还是依附于构建的意图而显现其意义? 对于马嘉人社会的真相,欧匹兹本人也是惶惑的,他尽力把研究的过程植入电影本身当中。在纪录片开头,插入了一些很短的影像序列,由混杂的元素组成,一部分是故事,一部分是介绍之后忽然显现在图像上的电影的主题对象,“ 这一部分叫做不安的人类学家的世界或序列——进入一种文化,却没什么收获。” 这可能能够部分回答上述的问题,人类学研究不在于展示一个既定的答案,而在于呈现的过程。而我们观看民族志纪录片,也不在于收看一个逻辑自洽的故事,而是观看故事形成的过程,这可能不啻于对所谓真相的一种尊重。 文明,彼此之间 影片开头就介绍到:人类经历已过四个世纪,我们现在的第四世,恰好是“黑暗纪”,普遍的猜疑、混乱、嫉妒让人们失去了认识事物的眼睛,使我们看不到世界真正的价值,这就是影片名中“盲国”的由来。这一解说帮助我们从文明俯瞰的视野,聚焦到马嘉人这一方文明世界,让我们感知到任何一种文明只是处于整体文明的一个片段之中,彼此之间的连结也被关照到了。 在围绕该片展开的研讨会中,专家不止一次把有神论的“落后”文明与现代文明建立联系。陈传兴指出,我们可以看见一条乍看之下是线性的人类思想发展史,从诗的表达、神话的时代,到宗教形式、形式出现,偶像、神话退位,哲学的辩论开始,西方传统对于知识的定义和思辨出现。然而,许多思想家已经发现这条发展之路并非线性继续指向科学与理性的思想发展,而是一条环状的回溯之路。 我想,这无疑代表了一种史观,认为不同时期的文明是被有意义地连接在一起的,或者说时间如同是一个有意义的容器,盛放着诸多人类文明的片段。这种判断,在于对文明之间传播力和延续性的认可。如此看来,萨满文化部落如同是在一段时间内自外于文明光照的片段,凝结在了那个相信死后世界的过去。也因此,它便也成为返照在此处文明镜像之上的影子,从而显现了意义的丰富。 正如第一部结尾所表现的那样,现代文明的参照物被拿来与萨满比对,拍摄者问萨满,西医是否会影响到他的职业。现代性之光终于也普照到了这一地区。在不同文明之中,这两种职业是相互平行的。站在文化无优劣的立场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两种身份可以被等量齐观。两者都因为掌握在当地稀缺的知识而获得了特殊的身份。而不同点在于,西医始终立足于可见的世界,萨满却是不可见世界里的预卜先知。 萨满的存在代表了不可见世界存在的正当性。对不可知世界的恐惧和忧虑,化为驯服的言行,也意味着现实中的一种解药。除此之外,萨满与当地生产和社群之间维系了牢固地纽带,立足于唯心世界的身份同样参与了物质的生产和连结,这应当也是地位成立的证明。这可能也是我们站在自身的文化视角理解他们的方式,虽然在现代文明中还没有完美的替代者。 那个维度 回到纪录片,正是萨满带给我们关于那个世界的触觉和感知。 “ 即使你不信鬼神,也能感受到这份凝重。 ”欧匹兹说起他拍摄时候的感受,“ 起初便感受到了,在那样的状态下,你的感知会变得非常强烈,并且会期待接下来发生的事,仪式在环境中建立起的氛围会渐渐渗透到你的内心,让你感觉到自己完全参与其中。我不会说这是「参与式观察」,那就是一种参与到里头的感受,就像是个魔幻时刻,让人感觉到有什么被点亮了。 ”在那一时刻,他感知到了另一个空间维度的重量,这与其说是与马嘉人达到了共情,不如说是来自于原始本能的意识被唤醒了。 对此,云南人类学家郭净着重指出了纪录片中多维空间的存在。“最终,镜头变成了几乎可以自由穿梭在不同时空的神秘之眼。 欧匹茨本人,变成了一位神奇的萨满:他既能洞悉喜马拉雅山地民族的隐秘世界,也最终成了一个沟通外部、内部与秘密三个维度的,独具匠心的搭桥者。他想超越文化和修为对其自身的限制,抵达一个异文化的观察者通常无法进入的维度,达到对研究对象的深刻理解。” 这一评论运用了他的卡瓦格博民族志《雪山之书》当中的视角,雪山之中存在着可见的“世俗空间”和不可见的、令村民敬畏的“神圣空间”,但就纪录片而言,这无疑是一种高明的溢美之词,而要达到这样的观感,影视的美学表现力是其一,其次也取决于观众的悟性和世界观。 让我感到印象最为深刻的情节在第二部后半段,即将成为萨满的人被蒙上眼睛,在众人的簇拥和托举之下,爬上高耸的生命之树。一开始,其他萨满在树下唱诵和击鼓,而后他们回到村子享受丰盛大餐,他却要一个人面对孤独。他站在高高的木桩上,意味着他抵达了与天之间的界限,他会预知未来世界即将发生什么,这对于其他村民而言是不可知的,因为只有他是未来病人的灵魂治愈者。那是属于萨满的静默时间。 “在影片中,主角是时间,是史诗般的时间,马嘉人的生活对我来说像史诗一般。观众最终会爱上它,是因为观影时间,创建了一种关系,一种观众与电影之间无形的又很是奇妙的关系,参与效应,置身在活生生的经历里。”欧匹兹说。 在这个时间里,萨满行为的怪诞是不值得嗔怪的,我们会与村民们一样,深信那个片刻对于萨满的特殊意义,期待他会在一瞬间的微风和树叶摩擦的声音里,在灵光乍现的闪光,洞悉往后世间的去向。
猜你喜欢
- 超清
声名狼藉先生:我有故事要说
2021/美国/纪录片
- 超清
茶煲表哥:30年重聚
2020/美国/纪录片
- HD中字版
宇多田光首次录音棚演唱会
2022/日本/纪录片
当自由燃烧时
2020/美国/纪录片
- 更新至1集
梦想之大构建我们的世界
2017/美国/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