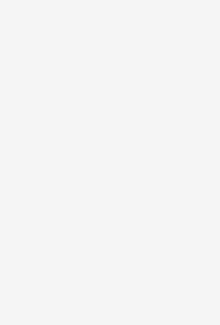我不属于任何地方-香特尔·阿克曼的电影 HD
分类:纪录片 地区:其它年份:2015
主演:香特尔·阿克曼,格斯·范·桑特
导演:玛丽安娜·兰伯特
更新:2023-08-06 21:09
简介:IDon’tBelongAnywhere-LeCinéma..IDon’tBelongAnywhere-LeCinémadeChantalAkerman,exploressomeoftheBelgianfilmmaker’s40plusfilms.FromBrusselstoTel-Aviv,fromParistoNew-York,thisdocumentarychartsthesitesofherperegrinations.Anexperimentalfilmmaker,anomad,ChantalAkermanshareshercinematictrajectory,onethathasneverceasedtointerrogatethethemeaningofherexistence.Thanksingreatparttotheinterventionsofhereditor,ClaireAtherton,shedelineatestheoriginsofherfilmlanguageandheraestheticstance. 前言 出生于1950年的比利时导演香特尔·阿克曼的电影以实验性的结构和女性主义所著称,但她本人却并不把自己的电影归类于此。在拍摄于2015年的纪录片《我不属于任何地方》中,她说:“我不想参加同志电影节、女性电影节或者犹太人电影节,我只想参加那些普通的电影节,我做的只是电影,仅此而已。” 《我不属于任何地方》剧照(2015) “电影就是我的自画像” 对于香特尔·阿克曼来说解释自己一直是困难的。在拍摄于1997年的《阿克曼自画像》中她选择以第三人称的身份来谈论自己,“希望致以真诚和勇气”。像她的电影主人公一样,她朝着固定机位,处于正面镜头里;语速吞吐、凝滞,像她电影中的那些空白。最后她将自己各个作品的片段剪辑在一起,以此作为“自画像”。“带着让我过去影片为自己说话的念头,我把它们当作样片剪辑成一部新片。这将成为我的自画像。” 到了2015年的纪录片《我不属于任何地方》,此时的阿克曼不再端正地坐在正面镜头中,她在餐厅吃着面包接受访谈;在轮船上和陌生人攀谈,分享记忆……作为观众,我们暂时被阿克曼邀请走进她的“时间”,并得以从其他角度的“机位”了解她。 《我不属于任何地方》剧照(2015) 她不再那么局促,也不再回避以第一人称来谈论自己的作品,言辞中甚至有一种急迫的坦诚。但这种转变似乎已隐隐流露出一种危险的气息(阿克曼在15年10月自杀),像站在悬崖边跳舞的人;一辆生锈的卡车开始急速晃动车后箱的果实。“我发现我母亲是我的拍摄里的核心,现在这里已经没有任何人了,所以现在我感到害怕,我不知道我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14年母亲的死亡像突然被撤走的坐标轴定点,摇摇欲坠地,阿克曼开始流淌出“部分的自己”。 “我的母亲是我创作的核心” 纪录片以海对岸的纽约景观拉开序幕,瞬时将我们带回1977年《家乡的消息》中的纽约。但与《家乡的消息》不同,当时锋利、冷静的读信声音如今变得粗粝、浑厚;而曾经躲在镜头后的阿克曼此时则作为电影的一部分出现在画面当中。她回忆起自己第一次从飞机上鸟瞰纽约全景,纽约的巨大和病态让她想起那些家里的琐事,那些大家都有的既相似又独特的小事。 在阿克曼看来正是这些日常生活的场景下面暗藏着人类更基本、也更隐秘的情感。于是在《家乡的消息》里她选择以朗读母亲寄来的家信(画外音)和纽约城市景观作为两条相辅相成的主线,至始至终阿克曼都没有出场,而是假借母亲的身份(读信的画外音)来向母亲传递自己无法言说的情感。 《家乡的消息》(1977)中的纽约 《我不属于任何地方》(2015)的纽约 生于世纪中点(1950年)的阿克曼和二战擦肩而过,幸存者女儿的身份一直让她背负着“劫后余生”的阴影,但与不愿谈论奥斯维辛的母亲不同,她选择主动走向那段时间,正视它,以自己的声音填补缺席的解释。 在纪录片中,阿克曼的两部代表作《让娜·迪尔曼》和《我的城市》被并置在一起。当《我的城市》中的阿克曼在厨房疯狂地往自己脸上涂抹奶油,用煤气点燃花束,画面紧接着转到《让娜·迪尔曼》中躺在床上,沉默地进行性交易的女主人公;而当《我的城市》中的厨房最终被烧毁,画面又切到起身默默地穿上衣服后一刀刺死嫖客的迪尔曼。一个是暴力的撕裂,在夜间失控的火车头最后撞向树;一个是沉默中的反抗,一根拉长的细铁丝最后崩裂。 《我的城市》剧照 《让娜·迪尔曼》剧照 阿克曼用这种方式连接自己和那个象征着母亲一辈,生活在重复和禁锢的时间里的“迪尔曼们”,同时表达自己面临的另一种“厨房困境”。“我是在替她说话,有时候我所说的是在反对她”。母亲就像迪尔曼一样,将自己的生活切割成精准的段落,每一点钟要干什么都了然于胸,但那些看起来庸常的“切土豆时间”里却隐藏着她们没有说出口的郁结。对于阿克曼来说,母亲的沉默,这份“空白”便是可以旋转起她的创作的永动机,她要踩进去,和这份“空白”在一起。 “跨境者阿克曼:对,我在这里,我也可以在别处” 破碎镜面中阿克曼的笑容 除了对母亲的情感,在《我不属于任何地方》中,通过阿克曼和其共事者的解读,再反观她的创作规律和人生,我们得以看见阿克曼的“不属于任何地方”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失去了母亲的比利时(“即使我在巴黎有个家,有时候也在纽约,但无论什么时候我说我要回家,我都是去我母亲那里,但现在再也没有家了。”)而是涵盖了时间、性别、身份认同等其他方面的维度。 不论是移民后代、犹太血统、同性恋者还是女性主义者,阿克曼本可以就任何一个身份在电影里大作一番文章,但她却没有如此。她并非拒绝这些身份(阿克曼十分强调事实,在《阿克曼的自画像》中她反复强调“我的名字是香特尔·阿克曼。我出生于布鲁塞尔。这是事实。这是事实。”)而是将她对这些议题的理解消化在电影的底色中,将核心让位于人本身。让她更为触动的不是《来自东方》(1993)背后的东欧政治文化,而是这种文化下,更隐蔽的情感“,他们等着车,像等着死亡。” 再比如在影片中,《安娜的旅程》主演奥萝尔·克莱芒回忆和阿克曼一起工作的细节,“我喜欢她接近人、身体、女性的方式;她对服装、高跟鞋的高度,甚至高跟鞋发出的声音的掌控。”阿克曼的女性主义并非来自于某种诉求,而是对作为人本身的女性,更深一步的注视。和维吉尼亚·伍尔夫一样,她带领观众(包括女性观众)走到那些不被注意,被吞没在大叙事下的日常细节里,通过这些看似冗长无味,难以忍受的场景,我们不得不正视真实的生活。 《安娜的旅程》中的女主角 在层层嵌套的车厢里仿佛在循环往复的时间里 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阿克曼对“时间”的理解。阿克曼在影片中回忆《非家庭电影》(2015)的剪辑过程,起初在他人的建议下她也打算对电影时长进行删减,但却发现删减后的镜头看起来平淡无奇,没有了那种时刻与时刻之间的紧张感。她希望打破观众对“时间”的惯性认知,以独特的剪辑方式、画面构图确立属于“她的时间”。“我不会去做特写,而是拍摄一整个场景,很多导演不给观众自由去做他想做的,我做相反的事,我希望观众可以自由地去感受电影,而不单单是去理解。”(对于演员阿克曼同样如此,她希望演员可以更在自己的状态里,而非跟着导演的指导走。)打开问题远比给出答案吸引阿克曼。 你知道,对于大部分去看电影的人来说,对影片的终极褒奖便是——“我们并未感觉到时间的流走。”而对我来说,观众在我的影片里目睹着时间的经过、并感觉到它。它们让你感受到这便是流向死亡的时间。我想,我的影片里确实有那么一种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有如此多的观众对此产生了抗拒。我取走了他们生命中的两小时时间。—— 香特尔·阿克曼答巴黎作家米里亚姆·罗森问。 阿克曼的这种试图跨越边界的意志还体现在她对虚构和纪实的理解里。和阿涅斯·瓦尔达一样,她们都认为好的虚构电影中应该有一些记录元素,反过来亦然。对于阿克曼来说如何更好地表达电影的核心要比使用哪种技术、是否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等要来得重要地多。电影变成她的实验田,“一开始我拍片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愿想,我希望自己像一个海绵一样去吸收。”她就像自己的影片《在那一边》的跨境者,在各种题材、虚构与纪实、不同身份认同等各种边界游走,而正是这种“无从定义”定义了她,带她走向特属于自己的“叙事方式”。 向新的“空白”走去 阿克曼一直没有给自己预设方向,或抱着向观众传达某个答案的想法,相反,她保留了自己的困惑,“我围绕着电影来写,围绕着那个空洞——或者说是,空缺。”而她的珍贵之处正在于没有取捷径走向“答案”,而是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空缺。 在《我不属于任何地方》的海报里,香特尔·阿克曼独自坐在巨大的废铁器上,一边迎着沙漠的风,一边诉说着她的故事,就像在大家看来那些历史已经过去,但她却仍要和“废墟”在一起,和时间里的“淤积块”对话。在电影最后的画面里,她走下废铁器,向公路的远方走去,仿佛向着新的“空白”走去。 《我不属于任何地方》剧照(2015) 在纪录片中,阿克曼以画外音的形式朗读了一段循环式的童谣,最后一节是: 拉比的曾曾孙不知道树 不知道林,不知道村子在哪 甚至不记得祷告的话 但他仍知道这个故事 因此,他把故事告诉自己的孩子 而上帝听到了他 即便故事的细节被时间吞没,但只要有人在继续说这些故事,就会有人会重新踏进这个环中,寻找它。 撰文|林翠羽 校对 |杜茜 王施澳 购票链接请点击:公布 | 2019山一排片单及抢票攻略 相关链接:公布 | 2019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完整片单
“非凡女性”单元 | 反抗、遗忘和死亡:三位女导演的传奇电影人生
“全球狂潮”单元 |女性电影与目光
“华语力量”单元 | “女人是‘一切无’”,是自由
特别鸣谢 官方指定酒店 成都博舍酒店 官方网站:www.oneiwff.com
官方邮箱:contact@oneiwff.com 官方微博: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 官方微店: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 版权说明:所有原创文章版权归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所有,感谢喜欢的朋友转发,转发时请注明出处。用于商业用途时,请务必联系我们。
猜你喜欢
- 超清
声名狼藉先生:我有故事要说
2021/美国/纪录片
- 超清
茶煲表哥:30年重聚
2020/美国/纪录片
- HD中字版
宇多田光首次录音棚演唱会
2022/日本/纪录片
当自由燃烧时
2020/美国/纪录片
- 更新至1集
梦想之大构建我们的世界
2017/美国/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