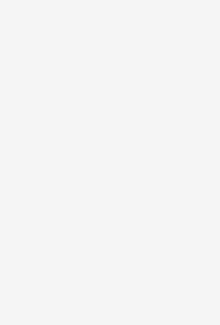罗拉 超清
分类:剧情片 地区:其它年份:1981
主演:马里奥·阿多夫,巴巴拉·苏科瓦,阿明·缪勒-斯塔尔
导演: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
更新:2023-05-02 21:49
简介:故事发生在五十年代中期,身为夜总会里的当红头牌,温柔美艳的..故事发生在五十年代中期,身为夜总会里的当红头牌,温柔美艳的罗拉(芭芭拉·苏科瓦BarbaraSukowa饰)每日都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舒克尔(马里奥·阿多夫MarioAdorf饰)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地产大亨,他还有着另一个身份——罗拉...{if:" 《萝拉》是法斯宾德“西德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改编自约瑟夫·冯·斯登堡导演的《蓝色天使》。电影讲述的故事十分古典和类型化——男主角伯赫(Bohm)是一位传统、守常的实干派,作为建筑专员(Building commissioner)被聘至西德的某小城,当时正值联邦德国首届总理阿登纳任内,在战后百废待兴、经济快速复苏的格局背后,是一系列腐败、通货膨胀、阶级分化等社会现象;权贵敛缩在当地一家风月场中,窃弄着指间的权柄,极尽嬉靡之事;女主角萝拉是该地的歌女,由于和情夫(也是老主顾)“包工头”舒克特(Schuckert)之间的一次赌注,她主动结识了男主,也将蓄藏着引诱、挚爱、背叛、耻辱和堕落的休弥尔酒杯一道打碎。 相比罗恰、戈达尔、吉田喜重等人隐晦、艰诘的政治诉求,导演法斯宾德在影片中并没有刻意表达出个人的意识形态倾向;即使设置了热衷巴枯宁(却反对革命)的人文主义者伊斯林(Esslin)叛离理想、甘愿成为新权贵这一插曲,但它也仅仅是当时多种思潮冲击下割裂的、混乱的政治局势的浅显表现。因此,与其说《萝拉》是一部政治题材电影,称之为一部有关爱情在权欲和物欲下幻灭的黑色电影可能更为合适。伊斯林(左)和市长(右),两者在片头时的首次同框.该段落是颇具戏剧性的,因为后者是前者的雇主,但因不想在风月场中被旁人发现正匆忙躲进厕所隔间内. 或许是为了招显自身的魅力,或许是为了她这种人(“He’s just not the man for Someone like you”)鲜薄的一丝尊严,萝拉和舒克特订下赌约,如果老派的伯赫肯用老派的礼节亲吻她的手,那么舒克特将献上十瓶香槟酒作为赔礼。由于诚服于伯赫的人性光辉,萝拉在赢得赌注后仍然同他保持着幽纷的关系。她最终疲惫的游走于伯赫和舒克特之间。在伯赫面前,她是爱好东亚艺术(Indirectly)的神秘贵妇,烂漫又不失持重;在舒克特面前,她则是酗酒、聒吵的娼妓。在多起故事冲突后,萝拉倾饮着双重身份为她带来的苦酒,尊严和爱的复归让她不忍心再欺骗伯赫。在寄出“Every song has an end”的告别信后,萝拉在风月场中做出了近乎疯癫的独唱。她撕扯着衣袂,影片也迎来了第一个高潮。她高唱着“I’ll be back tomorrow, be true to me. Don’t foget me, ”并未注意到远处被伊斯林“蛊惑”而来的伯赫,而后者正欲离开这个首次光顾的风月场,也正欲离开这位“首次”见到的萝拉. 一段小插曲,即在萝拉独唱之前,伯赫殷喜于面前这台新购进的电视机(当时联邦德国只有1个频道,仅在晚八点后播出).同室的美国租客炫耀“美国有12个频道”.伯赫脱口而出“我们德国也有两个频道”.西德、东德,两个德国,两个萝拉,值得玩味. 然而,段落间衔接的张力不足、叙事节奏的跳脱(当然,这在法斯宾德的电影中很是常见),使得影片的结尾略显突兀。故事最后,“Old-fashioned”的伯赫为了萝拉,选择迎附时代的潮流,放弃揭发战后重建工程内有关权钱交易的诸多丑闻,同伊斯林一样,叛卖了其消灭权贵阶级的理想(因为萝拉的栖身地正是该阶级的产物),选择同舒克特合作;萝拉则被伯赫从风月场中赎出,曾经的老主顾们为他们举办了一场庄严济跄的婚礼。重拾清誉的萝拉并没有裹足不前,依旧同舒克特保持着隐秘的情人关系,依照台词,她现在是一名“A rather expensive mistress”。作为对萝拉顾念旧情以及扶急持倾的奖励,舒克特为她奉上了一份结婚礼物——他买下了那座风月场。当然,现在的它,应该叫作“沙龙”。 虽然影片的结尾在处理上似乎陷入了一种“为了悲剧而悲剧”的执念,但本篇废话的重点并不在于这些故事冲突的转折和处理。如果仅仅言谈剧情,实在是渎慢了法斯宾德的天才。作为极具戏剧式风格的导演,法斯宾德并没有沿用其《当心圣妓》里犹如重度强迫症一般近乎完美的内景调度,《世界旦夕之间》中繁复的运动镜头或是《中国轮盘》内疯魔化的台词处理,而是引用了戏剧中“舞台”或是“舞台幻境”这一概念。电影全片几乎仅围绕着三处场景——风月场、市政办公厅以及伯赫的租屋来进行,段落间的转场大多采用极简的跳接或淡入淡出,似乎在模仿舞台上帷幕的作用。萝拉和舒克特,风月场,主色调为红色 伊斯林(前)和伯赫(后),市政办公厅,主色调为黄色 伯赫、管家和小玛丽,租屋,主色调为蓝色.值得一提的是,剧照中的管家是萝拉的母亲,小玛丽是萝拉和舒克特的私生女. 相比朴素的场景及场景间的切换,法斯宾德在布景和布光中则尽其所长,进行了复杂甚至堪称华丽的美术设置:对红、黄、蓝三原色的大量使用和搭配,色彩意象间的隔断和衔接,光线明暗和角度处理带来的显著的视觉差异,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隐喻、升华了故事的文本属性。下面我将从几个方面简单分析法斯宾德是如何通过美术设计对剧情予以补完的:三原色——恒定的独立关系和色彩意象 “A man has many faces. His everyday face, his Sunday face. Today I don’t want to look everyday.” 这是伯赫在电影中的一段台词。人在与社会联结的过程中,会根据其所处环境、接触人群和发挥功能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属性,即文中的“面孔”。伯赫在工作中是一丝不苟的,办事雷厉风飞,永不迟到的同时会呵责年迈的女秘书,让其每天比他提前一分钟到办公室;而他生活上却是谦和的,会跟孩子讲些毫无笑点的老旧笑话。伊斯林白天是“城市规划处的小小职员”,晚上却是反战组织的成员和风月场的鼓手。而萝拉不同面孔间的差异性则更加明显。在这里,导演用相互完全独立的原始三色对上述“面孔”的差异进行了区分,并通过考究的布光,暗中诱导观众产生相应的心理感觉。五个以上的背景光源让玻璃窗上方、后方均布满低饱和度的黄褐色;清冷的主副白光赋予最低限度的明亮感,画幅之外隐藏的条形射灯让墙壁现出曼妙的橄榄灰色,减弱了黄光的集中度.整体画面强调着一种暗沉的、古板的感觉,似乎在映射伯赫的工作态度和被动的局面. 生活上的伯赫是轻松、自然、沉着的,天然光的介入让整体画面明亮许多.左侧墙壁使用了小面积的天蓝色(饱和度较高),后方则是大面积的粉蓝色(饱和度较低),颜色层次间的递减配以仅发挥衬映作用的主光弱化了视觉冲击力,一眼看去很是舒适.左前方入镜的灯罩与人物和后方的台灯分布在近似纵向等分的四 伯赫在独处时是理性的,画面的主色调采用了凸显这种深邃气质的钢蓝色.辅光的缺失让伯赫的面孔呈现出经典的梅尔维尔式明暗造型.此时的他刚刚和萝拉约会完回到家中,左侧的墙壁是红蓝浸染后的紫罗红色,似乎预示着萝拉已进入伯赫的生活,而刻意打上的弱光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红色是热烈的、胶着的,它是三原色里和人最契合的颜色.红色血液的湓涌能让人类得以生存的同时,也带来了本能的冲动.萝拉所在的风月场是冲动的集合体:性和征服,物质和阶级,但兽欲的过度宣泄带来的只能是堕落与毁灭.场景内原本欢悦的红色在低明度处理下变成了猩红,显得神秘、污浊、狂乱,还带着几 需要强调的是,色彩意象是主观性极强的心理感受,上述画面的解读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和拙见。本人极度不欢迎“阅读理解式”的影评(像我这种吹毛求疵般自娱自乐还是可以的~~( ﹁ ﹁ ) ~~~),更不欢迎“马首是瞻”式的对他人观点的趋同。电影架构出的世界是极度开放的,它需要的永远都只是观众的眼和心,而不是所谓的点评。三原色——对比和衔接间高尚的和美 色彩作为二维艺术(电影也是)中继线条、光影(两者负责建立空间、确立造型)之后的填充和铺衬元素,可以直接的激发人的观感。自彩色电影开创不足七十年的岁月里,能够合理恰当运用色彩的大师并不多见。《卑弥呼》,筱田正浩,日本,1974 不同于阿莫多瓦、贾曼、筱田正浩、格林纳威等导演运用堆叠、拼接、支离、几何化等处理手段,将色彩运用在滤镜、布景、装置和服装之上,法斯宾德在《萝拉》中大多通过布光上对比度与深浅的过渡,将已经确立属性的独立色块进行写意的接合,以此实现一种至简与厚重的美。 这里是萝拉和伯赫初见时的场景.萝拉开着敞篷轿车穿过拱门,下车后正向参加剪彩仪式的伯赫走去.墙上的红光在后方明丽的浅黄色建筑掩映下变得可有可无,两道拱门共同组成起框架,似乎分割出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巧妙设计的修饰光配以景深作用下模糊的黄色背景,突出了伯赫近景中的蓝色瞳孔. 此处是被多位影评人津津乐道的一个段落.斜上方处的光源经过滤光、遮挡等处理,使光线在两人之间形成了强烈的“白(蓝)-红”对比.此刻萝拉正对伯赫约会前精心挑选的衣服进行点评,她并不喜欢这件衣服,因为它和伯赫平日的呆板风格不一样.这让她觉得不“真实”,而虚伪是这个城市以及其中充斥着的骗 伯赫并不相信,萝拉却让他在自己“灵魂进一步显现前”赶紧离开.两人正欲吻别时,却被一道眩目的车灯打断了.没有秘密是可以在光下掩藏的.后面的剧情也证明了这一点. 伯赫在知晓萝拉的秘密后,痛恨权贵阶级将自己心爱的女人视作可以买卖的玩物,于是中断了策划的战后重建项目,并搜集权贵们腐败的证据意图揭露.难以自保的舒克特“劝慰”伯赫,萝拉先前的美好全是假象,她只是一个有钱就能使唤的娼妓.于是伯赫第二次来到风月场,当他发现自己还是无法将感情变成一桩买 三原色——过渡与终结 除去三原色的大量出现,法斯宾德还在某些场景内间杂了二次色的使用,如上图伯赫选衣时布景选用的紫罗兰色+淡紫色(蓝+红),下图办公室窗外的绿色光源(蓝+黄)。是有意为之,借基本的调色原理对情节和人物心理活动进行渲染;还是仅仅出于美术需要,这大概只有导演本人才能回答 (ーー゛)。 而在某些重要的转折点,法斯宾德则使用了与前期基调完全不同的配色,丰富人物细节的同时,也对后续剧情发展提供了暗示。对于这部叙事较为松散的《萝拉》,这些被捕捉到的,有关导演本人微小的镜头流露,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厘清故事的逻辑内核。伯赫奏起萝拉独唱的那首歌(前一个镜头即是舒克特让他去用金钱征服萝拉).正侧光作为主光,将舒赫右脸眼窝外的垂直面全部打亮,辅光则选择了前顶光,亮度较低,仅突出了舒赫眼部周围.主辅光的结合在人物脸部形成了较为强烈的明暗差,打光位置的不同突出了主体脸部细节(尤其是眼睛),加重了表情刻画 此时的萝拉正在电话里为伯赫读情书.屋内的场景不再是单一的猩红,而是在滤光片或是色纸的拼接下,被各种色块所分割,形成极度迷幻、斑斓的色彩组合;低明度的布光处理弱化了不同色相间的差别,使画面整体的色调统一而暧昧.特别设置的镜子则加强了反射,使床单的颜色更加错杂,同时延展了空间的纵深度 这是萝拉房间内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反常规的配色.穿着红衣(同样是房间内的第一次)的萝拉因想着要作别伯赫而闷闷不乐,身后的伊斯林正在追问原因.除去萝拉发端处的轮廓光,镜像内没有亮度更强的用光,这使得两侧的灯柱成为视觉主体,鲜明的颜色(红、黄、蓝以及间色)很好的活跃了画面的整体氛 从这两处细节,我能感受到导演对于萝拉的爱(或者是善良)的态度是积极的。遗憾的是,我并没有找到她在结尾处再次转变的动机。唯一的线索便是萝拉自言的那句“我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从来没有让我真的加入过(这个丧失道德,罪恶、堕落和腐败的世界)”。然而,萝拉面对痛苦的伯赫时,还是惊讶的说出了一句“你真的爱我”。 同样是真的,前者未免也太苍白了。 大概是法斯宾德对当时西德的现状过于痛恨了吧。无论如何,在影片结尾,萝拉正在婚房内同舒克特调情(画面内又出现了氤氲的红色)。而伯赫则在教堂旁的木屋出神,这里正是他和萝拉定情的地方,一侧的伊斯林问他感觉如何—— “一切都很好。”伯赫答道。 背景中的小玛丽像极了天使,毕竟红、黄、蓝加起来,便是那至高的黑色,就像舒克特坐着的那张沙发。悠闲的舒克特 仅以此篇废话,向伟大的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以及他致敬的亚历山大·克鲁格致敬!"<>"" && " 《萝拉》是法斯宾德“西德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改编自约瑟夫·冯·斯登堡导演的《蓝色天使》。电影讲述的故事十分古典和类型化——男主角伯赫(Bohm)是一位传统、守常的实干派,作为建筑专员(Building commissioner)被聘至西德的某小城,当时正值联邦德国首届总理阿登纳任内,在战后百废待兴、经济快速复苏的格局背后,是一系列腐败、通货膨胀、阶级分化等社会现象;权贵敛缩在当地一家风月场中,窃弄着指间的权柄,极尽嬉靡之事;女主角萝拉是该地的歌女,由于和情夫(也是老主顾)“包工头”舒克特(Schuckert)之间的一次赌注,她主动结识了男主,也将蓄藏着引诱、挚爱、背叛、耻辱和堕落的休弥尔酒杯一道打碎。 相比罗恰、戈达尔、吉田喜重等人隐晦、艰诘的政治诉求,导演法斯宾德在影片中并没有刻意表达出个人的意识形态倾向;即使设置了热衷巴枯宁(却反对革命)的人文主义者伊斯林(Esslin)叛离理想、甘愿成为新权贵这一插曲,但它也仅仅是当时多种思潮冲击下割裂的、混乱的政治局势的浅显表现。因此,与其说《萝拉》是一部政治题材电影,称之为一部有关爱情在权欲和物欲下幻灭的黑色电影可能更为合适。伊斯林(左)和市长(右),两者在片头时的首次同框.该段落是颇具戏剧性的,因为后者是前者的雇主,但因不想在风月场中被旁人发现正匆忙躲进厕所隔间内. 或许是为了招显自身的魅力,或许是为了她这种人(“He’s just not the man for Someone like you”)鲜薄的一丝尊严,萝拉和舒克特订下赌约,如果老派的伯赫肯用老派的礼节亲吻她的手,那么舒克特将献上十瓶香槟酒作为赔礼。由于诚服于伯赫的人性光辉,萝拉在赢得赌注后仍然同他保持着幽纷的关系。她最终疲惫的游走于伯赫和舒克特之间。在伯赫面前,她是爱好东亚艺术(Indirectly)的神秘贵妇,烂漫又不失持重;在舒克特面前,她则是酗酒、聒吵的娼妓。在多起故事冲突后,萝拉倾饮着双重身份为她带来的苦酒,尊严和爱的复归让她不忍心再欺骗伯赫。在寄出“Every song has an end”的告别信后,萝拉在风月场中做出了近乎疯癫的独唱。她撕扯着衣袂,影片也迎来了第一个高潮。她高唱着“I’ll be back tomorrow, be true to me. Don’t foget me, ”并未注意到远处被伊斯林“蛊惑”而来的伯赫,而后者正欲离开这个首次光顾的风月场,也正欲离开这位“首次”见到的萝拉. 一段小插曲,即在萝拉独唱之前,伯赫殷喜于面前这台新购进的电视机(当时联邦德国只有1个频道,仅在晚八点后播出).同室的美国租客炫耀“美国有12个频道”.伯赫脱口而出“我们德国也有两个频道”.西德、东德,两个德国,两个萝拉,值得玩味. 然而,段落间衔接的张力不足、叙事节奏的跳脱(当然,这在法斯宾德的电影中很是常见),使得影片的结尾略显突兀。故事最后,“Old-fashioned”的伯赫为了萝拉,选择迎附时代的潮流,放弃揭发战后重建工程内有关权钱交易的诸多丑闻,同伊斯林一样,叛卖了其消灭权贵阶级的理想(因为萝拉的栖身地正是该阶级的产物),选择同舒克特合作;萝拉则被伯赫从风月场中赎出,曾经的老主顾们为他们举办了一场庄严济跄的婚礼。重拾清誉的萝拉并没有裹足不前,依旧同舒克特保持着隐秘的情人关系,依照台词,她现在是一名“A rather expensive mistress”。作为对萝拉顾念旧情以及扶急持倾的奖励,舒克特为她奉上了一份结婚礼物——他买下了那座风月场。当然,现在的它,应该叫作“沙龙”。 虽然影片的结尾在处理上似乎陷入了一种“为了悲剧而悲剧”的执念,但本篇废话的重点并不在于这些故事冲突的转折和处理。如果仅仅言谈剧情,实在是渎慢了法斯宾德的天才。作为极具戏剧式风格的导演,法斯宾德并没有沿用其《当心圣妓》里犹如重度强迫症一般近乎完美的内景调度,《世界旦夕之间》中繁复的运动镜头或是《中国轮盘》内疯魔化的台词处理,而是引用了戏剧中“舞台”或是“舞台幻境”这一概念。电影全片几乎仅围绕着三处场景——风月场、市政办公厅以及伯赫的租屋来进行,段落间的转场大多采用极简的跳接或淡入淡出,似乎在模仿舞台上帷幕的作用。萝拉和舒克特,风月场,主色调为红色 伊斯林(前)和伯赫(后),市政办公厅,主色调为黄色 伯赫、管家和小玛丽,租屋,主色调为蓝色.值得一提的是,剧照中的管家是萝拉的母亲,小玛丽是萝拉和舒克特的私生女. 相比朴素的场景及场景间的切换,法斯宾德在布景和布光中则尽其所长,进行了复杂甚至堪称华丽的美术设置:对红、黄、蓝三原色的大量使用和搭配,色彩意象间的隔断和衔接,光线明暗和角度处理带来的显著的视觉差异,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隐喻、升华了故事的文本属性。下面我将从几个方面简单分析法斯宾德是如何通过美术设计对剧情予以补完的:三原色——恒定的独立关系和色彩意象 “A man has many faces. His everyday face, his Sunday face. Today I don’t want to look everyday.” 这是伯赫在电影中的一段台词。人在与社会联结的过程中,会根据其所处环境、接触人群和发挥功能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属性,即文中的“面孔”。伯赫在工作中是一丝不苟的,办事雷厉风飞,永不迟到的同时会呵责年迈的女秘书,让其每天比他提前一分钟到办公室;而他生活上却是谦和的,会跟孩子讲些毫无笑点的老旧笑话。伊斯林白天是“城市规划处的小小职员”,晚上却是反战组织的成员和风月场的鼓手。而萝拉不同面孔间的差异性则更加明显。在这里,导演用相互完全独立的原始三色对上述“面孔”的差异进行了区分,并通过考究的布光,暗中诱导观众产生相应的心理感觉。五个以上的背景光源让玻璃窗上方、后方均布满低饱和度的黄褐色;清冷的主副白光赋予最低限度的明亮感,画幅之外隐藏的条形射灯让墙壁现出曼妙的橄榄灰色,减弱了黄光的集中度.整体画面强调着一种暗沉的、古板的感觉,似乎在映射伯赫的工作态度和被动的局面. 生活上的伯赫是轻松、自然、沉着的,天然光的介入让整体画面明亮许多.左侧墙壁使用了小面积的天蓝色(饱和度较高),后方则是大面积的粉蓝色(饱和度较低),颜色层次间的递减配以仅发挥衬映作用的主光弱化了视觉冲击力,一眼看去很是舒适.左前方入镜的灯罩与人物和后方的台灯分布在近似纵向等分的四 伯赫在独处时是理性的,画面的主色调采用了凸显这种深邃气质的钢蓝色.辅光的缺失让伯赫的面孔呈现出经典的梅尔维尔式明暗造型.此时的他刚刚和萝拉约会完回到家中,左侧的墙壁是红蓝浸染后的紫罗红色,似乎预示着萝拉已进入伯赫的生活,而刻意打上的弱光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红色是热烈的、胶着的,它是三原色里和人最契合的颜色.红色血液的湓涌能让人类得以生存的同时,也带来了本能的冲动.萝拉所在的风月场是冲动的集合体:性和征服,物质和阶级,但兽欲的过度宣泄带来的只能是堕落与毁灭.场景内原本欢悦的红色在低明度处理下变成了猩红,显得神秘、污浊、狂乱,还带着几 需要强调的是,色彩意象是主观性极强的心理感受,上述画面的解读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和拙见。本人极度不欢迎“阅读理解式”的影评(像我这种吹毛求疵般自娱自乐还是可以的~~( ﹁ ﹁ ) ~~~),更不欢迎“马首是瞻”式的对他人观点的趋同。电影架构出的世界是极度开放的,它需要的永远都只是观众的眼和心,而不是所谓的点评。三原色——对比和衔接间高尚的和美 色彩作为二维艺术(电影也是)中继线条、光影(两者负责建立空间、确立造型)之后的填充和铺衬元素,可以直接的激发人的观感。自彩色电影开创不足七十年的岁月里,能够合理恰当运用色彩的大师并不多见。《卑弥呼》,筱田正浩,日本,1974 不同于阿莫多瓦、贾曼、筱田正浩、格林纳威等导演运用堆叠、拼接、支离、几何化等处理手段,将色彩运用在滤镜、布景、装置和服装之上,法斯宾德在《萝拉》中大多通过布光上对比度与深浅的过渡,将已经确立属性的独立色块进行写意的接合,以此实现一种至简与厚重的美。 这里是萝拉和伯赫初见时的场景.萝拉开着敞篷轿车穿过拱门,下车后正向参加剪彩仪式的伯赫走去.墙上的红光在后方明丽的浅黄色建筑掩映下变得可有可无,两道拱门共同组成起框架,似乎分割出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巧妙设计的修饰光配以景深作用下模糊的黄色背景,突出了伯赫近景中的蓝色瞳孔. 此处是被多位影评人津津乐道的一个段落.斜上方处的光源经过滤光、遮挡等处理,使光线在两人之间形成了强烈的“白(蓝)-红”对比.此刻萝拉正对伯赫约会前精心挑选的衣服进行点评,她并不喜欢这件衣服,因为它和伯赫平日的呆板风格不一样.这让她觉得不“真实”,而虚伪是这个城市以及其中充斥着的骗 伯赫并不相信,萝拉却让他在自己“灵魂进一步显现前”赶紧离开.两人正欲吻别时,却被一道眩目的车灯打断了.没有秘密是可以在光下掩藏的.后面的剧情也证明了这一点. 伯赫在知晓萝拉的秘密后,痛恨权贵阶级将自己心爱的女人视作可以买卖的玩物,于是中断了策划的战后重建项目,并搜集权贵们腐败的证据意图揭露.难以自保的舒克特“劝慰”伯赫,萝拉先前的美好全是假象,她只是一个有钱就能使唤的娼妓.于是伯赫第二次来到风月场,当他发现自己还是无法将感情变成一桩买 三原色——过渡与终结 除去三原色的大量出现,法斯宾德还在某些场景内间杂了二次色的使用,如上图伯赫选衣时布景选用的紫罗兰色+淡紫色(蓝+红),下图办公室窗外的绿色光源(蓝+黄)。是有意为之,借基本的调色原理对情节和人物心理活动进行渲染;还是仅仅出于美术需要,这大概只有导演本人才能回答 (ーー゛)。 而在某些重要的转折点,法斯宾德则使用了与前期基调完全不同的配色,丰富人物细节的同时,也对后续剧情发展提供了暗示。对于这部叙事较为松散的《萝拉》,这些被捕捉到的,有关导演本人微小的镜头流露,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厘清故事的逻辑内核。伯赫奏起萝拉独唱的那首歌(前一个镜头即是舒克特让他去用金钱征服萝拉).正侧光作为主光,将舒赫右脸眼窝外的垂直面全部打亮,辅光则选择了前顶光,亮度较低,仅突出了舒赫眼部周围.主辅光的结合在人物脸部形成了较为强烈的明暗差,打光位置的不同突出了主体脸部细节(尤其是眼睛),加重了表情刻画 此时的萝拉正在电话里为伯赫读情书.屋内的场景不再是单一的猩红,而是在滤光片或是色纸的拼接下,被各种色块所分割,形成极度迷幻、斑斓的色彩组合;低明度的布光处理弱化了不同色相间的差别,使画面整体的色调统一而暧昧.特别设置的镜子则加强了反射,使床单的颜色更加错杂,同时延展了空间的纵深度 这是萝拉房间内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反常规的配色.穿着红衣(同样是房间内的第一次)的萝拉因想着要作别伯赫而闷闷不乐,身后的伊斯林正在追问原因.除去萝拉发端处的轮廓光,镜像内没有亮度更强的用光,这使得两侧的灯柱成为视觉主体,鲜明的颜色(红、黄、蓝以及间色)很好的活跃了画面的整体氛 从这两处细节,我能感受到导演对于萝拉的爱(或者是善良)的态度是积极的。遗憾的是,我并没有找到她在结尾处再次转变的动机。唯一的线索便是萝拉自言的那句“我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从来没有让我真的加入过(这个丧失道德,罪恶、堕落和腐败的世界)”。然而,萝拉面对痛苦的伯赫时,还是惊讶的说出了一句“你真的爱我”。 同样是真的,前者未免也太苍白了。 大概是法斯宾德对当时西德的现状过于痛恨了吧。无论如何,在影片结尾,萝拉正在婚房内同舒克特调情(画面内又出现了氤氲的红色)。而伯赫则在教堂旁的木屋出神,这里正是他和萝拉定情的地方,一侧的伊斯林问他感觉如何—— “一切都很好。”伯赫答道。 背景中的小玛丽像极了天使,毕竟红、黄、蓝加起来,便是那至高的黑色,就像舒克特坐着的那张沙发。悠闲的舒克特 仅以此篇废话,向伟大的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以及他致敬的亚历山大·克鲁格致敬!"<>"暂时没有网友评论该影片"} 《萝拉》是法斯宾德“西德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改编自约瑟夫·冯·斯登堡导演的《蓝色天使》。电影讲述的故事十分古典和类型化——男主角伯赫(Bohm)是一位传统、守常的实干派,作为建筑专员(Building commissioner)被聘至西德的某小城,当时正值联邦德国首届总理阿登纳任内,在战后百废待兴、经济快速复苏的格局背后,是一系列腐败、通货膨胀、阶级分化等社会现象;权贵敛缩在当地一家风月场中,窃弄着指间的权柄,极尽嬉靡之事;女主角萝拉是该地的歌女,由于和情夫(也是老主顾)“包工头”舒克特(Schuckert)之间的一次赌注,她主动结识了男主,也将蓄藏着引诱、挚爱、背叛、耻辱和堕落的休弥尔酒杯一道打碎。 相比罗恰、戈达尔、吉田喜重等人隐晦、艰诘的政治诉求,导演法斯宾德在影片中并没有刻意表达出个人的意识形态倾向;即使设置了热衷巴枯宁(却反对革命)的人文主义者伊斯林(Esslin)叛离理想、甘愿成为新权贵这一插曲,但它也仅仅是当时多种思潮冲击下割裂的、混乱的政治局势的浅显表现。因此,与其说《萝拉》是一部政治题材电影,称之为一部有关爱情在权欲和物欲下幻灭的黑色电影可能更为合适。伊斯林(左)和市长(右),两者在片头时的首次同框.该段落是颇具戏剧性的,因为后者是前者的雇主,但因不想在风月场中被旁人发现正匆忙躲进厕所隔间内. 或许是为了招显自身的魅力,或许是为了她这种人(“He’s just not the man for Someone like you”)鲜薄的一丝尊严,萝拉和舒克特订下赌约,如果老派的伯赫肯用老派的礼节亲吻她的手,那么舒克特将献上十瓶香槟酒作为赔礼。由于诚服于伯赫的人性光辉,萝拉在赢得赌注后仍然同他保持着幽纷的关系。她最终疲惫的游走于伯赫和舒克特之间。在伯赫面前,她是爱好东亚艺术(Indirectly)的神秘贵妇,烂漫又不失持重;在舒克特面前,她则是酗酒、聒吵的娼妓。在多起故事冲突后,萝拉倾饮着双重身份为她带来的苦酒,尊严和爱的复归让她不忍心再欺骗伯赫。在寄出“Every song has an end”的告别信后,萝拉在风月场中做出了近乎疯癫的独唱。她撕扯着衣袂,影片也迎来了第一个高潮。她高唱着“I’ll be back tomorrow, be true to me. Don’t foget me, ”并未注意到远处被伊斯林“蛊惑”而来的伯赫,而后者正欲离开这个首次光顾的风月场,也正欲离开这位“首次”见到的萝拉. 一段小插曲,即在萝拉独唱之前,伯赫殷喜于面前这台新购进的电视机(当时联邦德国只有1个频道,仅在晚八点后播出).同室的美国租客炫耀“美国有12个频道”.伯赫脱口而出“我们德国也有两个频道”.西德、东德,两个德国,两个萝拉,值得玩味. 然而,段落间衔接的张力不足、叙事节奏的跳脱(当然,这在法斯宾德的电影中很是常见),使得影片的结尾略显突兀。故事最后,“Old-fashioned”的伯赫为了萝拉,选择迎附时代的潮流,放弃揭发战后重建工程内有关权钱交易的诸多丑闻,同伊斯林一样,叛卖了其消灭权贵阶级的理想(因为萝拉的栖身地正是该阶级的产物),选择同舒克特合作;萝拉则被伯赫从风月场中赎出,曾经的老主顾们为他们举办了一场庄严济跄的婚礼。重拾清誉的萝拉并没有裹足不前,依旧同舒克特保持着隐秘的情人关系,依照台词,她现在是一名“A rather expensive mistress”。作为对萝拉顾念旧情以及扶急持倾的奖励,舒克特为她奉上了一份结婚礼物——他买下了那座风月场。当然,现在的它,应该叫作“沙龙”。 虽然影片的结尾在处理上似乎陷入了一种“为了悲剧而悲剧”的执念,但本篇废话的重点并不在于这些故事冲突的转折和处理。如果仅仅言谈剧情,实在是渎慢了法斯宾德的天才。作为极具戏剧式风格的导演,法斯宾德并没有沿用其《当心圣妓》里犹如重度强迫症一般近乎完美的内景调度,《世界旦夕之间》中繁复的运动镜头或是《中国轮盘》内疯魔化的台词处理,而是引用了戏剧中“舞台”或是“舞台幻境”这一概念。电影全片几乎仅围绕着三处场景——风月场、市政办公厅以及伯赫的租屋来进行,段落间的转场大多采用极简的跳接或淡入淡出,似乎在模仿舞台上帷幕的作用。萝拉和舒克特,风月场,主色调为红色 伊斯林(前)和伯赫(后),市政办公厅,主色调为黄色 伯赫、管家和小玛丽,租屋,主色调为蓝色.值得一提的是,剧照中的管家是萝拉的母亲,小玛丽是萝拉和舒克特的私生女. 相比朴素的场景及场景间的切换,法斯宾德在布景和布光中则尽其所长,进行了复杂甚至堪称华丽的美术设置:对红、黄、蓝三原色的大量使用和搭配,色彩意象间的隔断和衔接,光线明暗和角度处理带来的显著的视觉差异,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隐喻、升华了故事的文本属性。下面我将从几个方面简单分析法斯宾德是如何通过美术设计对剧情予以补完的:三原色——恒定的独立关系和色彩意象 “A man has many faces. His everyday face, his Sunday face. Today I don’t want to look everyday.” 这是伯赫在电影中的一段台词。人在与社会联结的过程中,会根据其所处环境、接触人群和发挥功能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属性,即文中的“面孔”。伯赫在工作中是一丝不苟的,办事雷厉风飞,永不迟到的同时会呵责年迈的女秘书,让其每天比他提前一分钟到办公室;而他生活上却是谦和的,会跟孩子讲些毫无笑点的老旧笑话。伊斯林白天是“城市规划处的小小职员”,晚上却是反战组织的成员和风月场的鼓手。而萝拉不同面孔间的差异性则更加明显。在这里,导演用相互完全独立的原始三色对上述“面孔”的差异进行了区分,并通过考究的布光,暗中诱导观众产生相应的心理感觉。五个以上的背景光源让玻璃窗上方、后方均布满低饱和度的黄褐色;清冷的主副白光赋予最低限度的明亮感,画幅之外隐藏的条形射灯让墙壁现出曼妙的橄榄灰色,减弱了黄光的集中度.整体画面强调着一种暗沉的、古板的感觉,似乎在映射伯赫的工作态度和被动的局面. 生活上的伯赫是轻松、自然、沉着的,天然光的介入让整体画面明亮许多.左侧墙壁使用了小面积的天蓝色(饱和度较高),后方则是大面积的粉蓝色(饱和度较低),颜色层次间的递减配以仅发挥衬映作用的主光弱化了视觉冲击力,一眼看去很是舒适.左前方入镜的灯罩与人物和后方的台灯分布在近似纵向等分的四 伯赫在独处时是理性的,画面的主色调采用了凸显这种深邃气质的钢蓝色.辅光的缺失让伯赫的面孔呈现出经典的梅尔维尔式明暗造型.此时的他刚刚和萝拉约会完回到家中,左侧的墙壁是红蓝浸染后的紫罗红色,似乎预示着萝拉已进入伯赫的生活,而刻意打上的弱光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红色是热烈的、胶着的,它是三原色里和人最契合的颜色.红色血液的湓涌能让人类得以生存的同时,也带来了本能的冲动.萝拉所在的风月场是冲动的集合体:性和征服,物质和阶级,但兽欲的过度宣泄带来的只能是堕落与毁灭.场景内原本欢悦的红色在低明度处理下变成了猩红,显得神秘、污浊、狂乱,还带着几 需要强调的是,色彩意象是主观性极强的心理感受,上述画面的解读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和拙见。本人极度不欢迎“阅读理解式”的影评(像我这种吹毛求疵般自娱自乐还是可以的~~( ﹁ ﹁ ) ~~~),更不欢迎“马首是瞻”式的对他人观点的趋同。电影架构出的世界是极度开放的,它需要的永远都只是观众的眼和心,而不是所谓的点评。三原色——对比和衔接间高尚的和美 色彩作为二维艺术(电影也是)中继线条、光影(两者负责建立空间、确立造型)之后的填充和铺衬元素,可以直接的激发人的观感。自彩色电影开创不足七十年的岁月里,能够合理恰当运用色彩的大师并不多见。《卑弥呼》,筱田正浩,日本,1974 不同于阿莫多瓦、贾曼、筱田正浩、格林纳威等导演运用堆叠、拼接、支离、几何化等处理手段,将色彩运用在滤镜、布景、装置和服装之上,法斯宾德在《萝拉》中大多通过布光上对比度与深浅的过渡,将已经确立属性的独立色块进行写意的接合,以此实现一种至简与厚重的美。 这里是萝拉和伯赫初见时的场景.萝拉开着敞篷轿车穿过拱门,下车后正向参加剪彩仪式的伯赫走去.墙上的红光在后方明丽的浅黄色建筑掩映下变得可有可无,两道拱门共同组成起框架,似乎分割出了两个不同的世界. 巧妙设计的修饰光配以景深作用下模糊的黄色背景,突出了伯赫近景中的蓝色瞳孔. 此处是被多位影评人津津乐道的一个段落.斜上方处的光源经过滤光、遮挡等处理,使光线在两人之间形成了强烈的“白(蓝)-红”对比.此刻萝拉正对伯赫约会前精心挑选的衣服进行点评,她并不喜欢这件衣服,因为它和伯赫平日的呆板风格不一样.这让她觉得不“真实”,而虚伪是这个城市以及其中充斥着的骗 伯赫并不相信,萝拉却让他在自己“灵魂进一步显现前”赶紧离开.两人正欲吻别时,却被一道眩目的车灯打断了.没有秘密是可以在光下掩藏的.后面的剧情也证明了这一点. 伯赫在知晓萝拉的秘密后,痛恨权贵阶级将自己心爱的女人视作可以买卖的玩物,于是中断了策划的战后重建项目,并搜集权贵们腐败的证据意图揭露.难以自保的舒克特“劝慰”伯赫,萝拉先前的美好全是假象,她只是一个有钱就能使唤的娼妓.于是伯赫第二次来到风月场,当他发现自己还是无法将感情变成一桩买 三原色——过渡与终结 除去三原色的大量出现,法斯宾德还在某些场景内间杂了二次色的使用,如上图伯赫选衣时布景选用的紫罗兰色+淡紫色(蓝+红),下图办公室窗外的绿色光源(蓝+黄)。是有意为之,借基本的调色原理对情节和人物心理活动进行渲染;还是仅仅出于美术需要,这大概只有导演本人才能回答 (ーー゛)。 而在某些重要的转折点,法斯宾德则使用了与前期基调完全不同的配色,丰富人物细节的同时,也对后续剧情发展提供了暗示。对于这部叙事较为松散的《萝拉》,这些被捕捉到的,有关导演本人微小的镜头流露,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厘清故事的逻辑内核。伯赫奏起萝拉独唱的那首歌(前一个镜头即是舒克特让他去用金钱征服萝拉).正侧光作为主光,将舒赫右脸眼窝外的垂直面全部打亮,辅光则选择了前顶光,亮度较低,仅突出了舒赫眼部周围.主辅光的结合在人物脸部形成了较为强烈的明暗差,打光位置的不同突出了主体脸部细节(尤其是眼睛),加重了表情刻画 此时的萝拉正在电话里为伯赫读情书.屋内的场景不再是单一的猩红,而是在滤光片或是色纸的拼接下,被各种色块所分割,形成极度迷幻、斑斓的色彩组合;低明度的布光处理弱化了不同色相间的差别,使画面整体的色调统一而暧昧.特别设置的镜子则加强了反射,使床单的颜色更加错杂,同时延展了空间的纵深度 这是萝拉房间内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反常规的配色.穿着红衣(同样是房间内的第一次)的萝拉因想着要作别伯赫而闷闷不乐,身后的伊斯林正在追问原因.除去萝拉发端处的轮廓光,镜像内没有亮度更强的用光,这使得两侧的灯柱成为视觉主体,鲜明的颜色(红、黄、蓝以及间色)很好的活跃了画面的整体氛 从这两处细节,我能感受到导演对于萝拉的爱(或者是善良)的态度是积极的。遗憾的是,我并没有找到她在结尾处再次转变的动机。唯一的线索便是萝拉自言的那句“我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从来没有让我真的加入过(这个丧失道德,罪恶、堕落和腐败的世界)”。然而,萝拉面对痛苦的伯赫时,还是惊讶的说出了一句“你真的爱我”。 同样是真的,前者未免也太苍白了。 大概是法斯宾德对当时西德的现状过于痛恨了吧。无论如何,在影片结尾,萝拉正在婚房内同舒克特调情(画面内又出现了氤氲的红色)。而伯赫则在教堂旁的木屋出神,这里正是他和萝拉定情的地方,一侧的伊斯林问他感觉如何—— “一切都很好。”伯赫答道。 背景中的小玛丽像极了天使,毕竟红、黄、蓝加起来,便是那至高的黑色,就像舒克特坐着的那张沙发。悠闲的舒克特 仅以此篇废话,向伟大的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以及他致敬的亚历山大·克鲁格致敬!{end 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