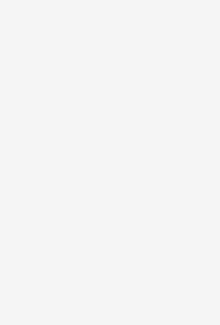乔·贝尔 超清
分类:剧情片 地区:美国年份:2020
主演:马克·沃尔伯格,里德·米勒,康妮·布里登,马克斯威尔·詹金斯,加里·西尼斯,摩根·莉莉,布莱恩·梅..
导演:雷纳尔多·马库斯·格林
更新:2023-02-18 15:21
简介: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雅丁(里德·米勒饰)因性取向遭受..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雅丁(里德·米勒饰)因性取向遭受同学的霸凌而自杀,他的父亲乔·贝尔(马克·沃尔伯格饰)由此展开了一场穿越美国之旅,在这场旅行中,乔·贝尔随时都能感受到雅丁就在他的身边。 和秋: 我第一次見到他的真人是2021年5月5日,因為這天是我到這個小店幫忙的第106天。這么多數字我怕一下子記不住,每天晚上吃完飯,什么事都不必想時就拿得這個黃軟皮本本,看一眼,然后在心劃拉劃拉看對不對。 我怕我第一百次忘了他。 來日本小雜貨鋪的那天是秋天。嗯?不應是2月里么,要認真算這也是大約母,那怎么都是在初春。但是我就是在來路上親眼目睹不止一片黃的深赭的枯樹葉子,從滿是葉子的樹上慢慢地墜落,最終掉在干干的地面。也許這一切現在想來都是緣,在春天應見萌芽的時分讓先見枯秋死了的葉子。這間鋪子我到現在都不全懂那幾個半截落塊的日文意思。一個倒彎勾,兩三個點添了豎條,再三個半圓圈的日字‘的’字,就一整個大和民族與中字最相通的那個寫法。我曾私下悄悄請教前輩,她嘴里嘟嚷完我還沒聽懂,只好最后干脆讓她翻譯出漢意,她說這叫小緣份。對,譯過來譯過去都是小的緣份,而不是仿日劇的諸如一眼瞬間,再見愛。即便真看懂日語的人憑字面會翻作再會緣。但我們看重的是它的內里,胖且白的姐姐神色凝重地看我說。我便不問,因為后來有幾次我見她午飯時間盯住牌名就是很久,擦了擦眼角后跟我去店外倉庫補貨。 它這里邊有縮小了一千倍的粉色購物車,散布夏夜黃昏野黃玫瑰氣的兒童版郵筒,我和它曾有一會,一個小朋友滿臉神秘叫過我來問這里邊究竟能裝進點什么,我隨口一說可以裝點豆子,他捂住嘴終于壓回笑容,走出店門轉了轉臉,給我一個詭異的笑,臉憋得幾近紫紅。難道這真的不能裝豆子么?我拿到天花板燈光下,剛在艷黃中一停手,筒蓋喝——撒——!一聲像篩下網筐的零豆,關上了。我于是特地挑了個粉嘟嘟的購物車和它一個水平比較,的確,筒的深度遠不跟筐可比,就眼下線筐也只能塞幾張便條紙,可我怎么一嚇就想到說豆子呢? 我回憶這一周吃過幾次豆子,都是黃豆,泡好和鹵雞蛋一塊兒燉,至少有三次,怪不得旁人一問我鬼使神差也先想到這個比喻,我的日子太乏味了。 為擺脫慣性,我盡量在店中沒人,貨也齊全最閑時盡量找些有意思的小物件觀察,免得給工作帶上情緒。但我用不上兩三天里一半的時間,就基本掌握了所有東西在的位置。花色帽子在那盞全店最黃的燈泡下,一排淺色,一排深,來到底全黑,但不便宜,曾有不斷的人來問回頭就走開;成縱列的購物筐我一盯好久,真想不出到底實用性在哪,只是淺淡燈管一照,好看得很,一些海灘,幾棵高大碧綠的棕櫚,帥哥,成群結隊,脖子套著救生圈,高大……我極時打消這種念頭,看不了太長一轉身,就張見不同年代的假人。復古的大麗花長裙子,大麗花!?那個美國懸慘案主,哦,我不能多想,剛才偏暖的向日葵花冠冷若冰霜。挨著她的紳士,我不喜歡,因為他泄頂,身邊卻仍有位捺著他瘦臂的優雅女士,她倒穿灰。一身淺線灰套裙,媽媽也有一件,每年只在春穿一次,后來我打開一遍衣櫥祭奠一回。往后幾層的小玩意我實在搞不清是些什么,往往是里三層外一層,機關復雜,包包裹裹,外表夢幻。我有時見人抽開,闔上,滿臉笑容,等他一走,我過去再依樣抽拉,左不過是動了番腦筋的存錢罐子。 有一樣小東西我挺喜歡,它印了些小人,都是日式帥哥,長劉海兒壓眉,高鼻梁,眼神細長、有情,腿長腰細肩寬的,每隔個木欞有一人,襯張霧紙,后邊中央有昏黃的燈,電一上的話,活了,一個接一個邁腿給你表演,迷幻的時光機,我就守著這燈,一個月過去沒有一人來問,但是我有空一看就呆一回。盯長了就好想,什么讓我這么癡迷,后來我明白了,這是種美,就算男性,到達一種安靜的狀態……我忽然覺得這和我到現在沒踫到戀愛有關,我想要是有天真有一個人,站在我面前,我就不會這樣想了,我的意思他要再長得特別特別好看的話。 兩個半月就這么流水過去,我手下小業務越來越熟,就是添貨,擺架使之美觀,偶爾忙不過來我去收銀,其他仍還是站著,站在頭頂那么多盞黃燈底下,漸漸感到一種慣性,正循舊路,但目前我也找不到克服的辦法,因此臉上漸漸帶出點老態。 他在這時出現了。 我永不會記錯那天他來的天氣,五月我大部分時間在穿那件墨綠色衣服,那天以前幾天我忽然想起幾年沒穿上的藏青高跟皮鞋了,拿出來打磨掉霉斑。第二天一早從那段大寬樓梯下去時他上來了。當時我感覺時間沒有了。我腳上的鞋子變得很重,而他一身白,因為抬腿邁臺子擋了一半的體子還是很高,細瘦有型。我從沒在這塊單調的地方見到過這么位帥的人。他看了我半眼我就和他先擦過肩,他的步子可真大啊。我再看眼下地,墨鏡里昏黃一片。他過去了,我也出了夢,走老路到那小店,當我再擺上那個小帥哥燈陣時,他回來了。 事后我去回憶,這很模糊。說是模糊,又很真實,很美好。我記住了他的體子。 成林: 我現在承認確實有點后悔,不該聽我發小的勸,先試試,我該去干快遞的,不是固定的人,見的都是新面孔,哪有這種圈里的窒息。我真有點喘不動氣,我過去從不相信有,但當我看到并發生在我身上,我責備自己走了眼,處世太淺薄。 我生怕處理不好這種關系。我人很單純,我一米九,但我的想法像小孩子,即便以后在社會上踢踏十年,我也還像是個大的學生。不是我傻,因為我不想把一切搞復雜,城府深,該躲躲,什么時候避得漂亮,讓他讓我顯得自然,我以前不這樣做人,現在也不。但是眼下我很痛苦。 我發現我被一個女人盯上了。她大概30歲上下,但她少相,兩鬢開得很寬,遠看近看極像夢露,是瑪麗蓮夢露式的臉型。她每次下來那個臺階,頭上載著黑的貝雷帽,她讓一角斜著,蓋了頭頂,洋氣得很。她很簡樸,直到現在,我只見她換過兩身,一淡駝色紗衣,短款,插肩,腰以上就沒,下邊一條黑底撒白雪點的長裙子。一件就是單純的暗紅運動衣,配個撮口紗黑褲。 記得她頭次盯我,我站在玻璃門外,我沒回頭,她一直看,我余光里有但不能轉身,以免被認為太敏感。但要這一次的話我就不會痛苦,接下去她隔了幾天后連著兩天坐到店對面的木桌,遠遠看,期間她每當我上貨要往那邊走,她照下我好幾次。我一聽快門響,就正對她鏡頭,這都是巧合,都在誤會。等到第三第四次的時候,她就直接坐到店另外一個出口——我常站著的正后門,那個紅方凳,我又不能因她而舍棄她身邊那個立柱有陰涼的優勢,我就成了常常站在她跟前的人。也就離她不到半米。她有時看那邊大超市來人,人都要往我這個沖大門方向走,眼光自然而然最終定位上我,上下走一遍,我這時身上很熱。有一次,她載的眼鏡累了往小椅上一擱,幾個連續的動作故作優雅,我正巧站乏了要走,一轉腰不經意間踫上這個端口,她也正抬頭,兩個目光對上,她一臉微笑,虔誠得很,嚇我及時改變了腳的方向。 那一整天都很熱。 有一次她竟然說話,問我你吃不吃巧克力的冰糕,我這里有,我看你害熱。我單沖她客氣笑了笑。 夢: 我的名字叫夢,最近幾年在夢里找不到媽媽,我醒后也不怎么傷心了,慢慢在適應。我年齡大了,期間又因為些事和身體方面原因,廣告業務員成了我最終記住的一個職業,而后就幫家里人買買菜,終生未婚。 提及終生未必到了八十高齡。但是從我內心已差不多就是個李紈,槁木死灰。 我買菜的路徑,自從搬到這個懸市區變多了點,一個仍是集,一個下兩條街或向東或向南走的小超市,一家二十來哩地外的大型超市。我無冬歷夏,大三伏天我騎在車子上也去。 小超市很擠,和在家里區別不大;集也沒上三年住的那個區的好,本地人軸,遠不及那里熱情;這個大超市還算行吧,因為它是我和母親生前年年去的那個海邊小城的連鎖超市,因此每到一個城市一見那三字心底五味雜陳。 一來太熱,二來我這幾年活得孤寂,我一坐就是半天,反正周末也沒事,回去那家也沒愛,也見不到想見的人。 我好像在第二次的時候曾見過一個很高的人,就在我身后那家日本店鋪。我并沒惡意,更不噬瀆,單純因美的緣故,好有時偶爾踫上多看這人兩眼。但很多時候都是他的身子回答,長腿細腰寬肩,標準的板兒,我那幾年常愛夸的日本男星體子。就只有一回,一種沒有聲音的對視,發生過也就過去了。 首先他很小,臉很單純,純真得很啊。也許又是年齡,我這種專注目光里滲點憾憐,可憐的份里有我想一直成為的人的意思。有天眼見他頭臉生熱的,手兜里剛買的冰糕又多了支,就說了句傻話,沒得到該得的簡單回應。我想是他復雜了。這是我的錯。 和秋每天早上作息時間是這樣,6點起床,7點一切完畢,過五分正出門,晚上,也就是夜11點半以后堅持原地跑,減肥。 成林每天的作息是這樣,5:30起床,5:40洗漱完出門進行一次慢長跑,范圍是他家兩條街區的龍盤山森林公園,6:30分回到家吃飯,7:30分出門因為離小店近,騎單車40分鐘。 夢的生活相對乏味,因為白天從不午休,一本書一本地接力看,頭疼是長久課題。除此之外是買菜-做飯-買菜-做飯,無限循環,吃飯-看書-吃飯-看書,眼鏡使了十年,去年秋換下,圓型鏡片一圈一圈。 一天,和秋聽見窗外鷓鴣枯寂的啾聲,起早了,秋天到了,她回憶起一棵美妙的樹。昨天回家晚,行人已不多,她得以在那株樹下小待,還是梧桐。眨眼間有了光線,藏在樹的高處,一個點子,一串亮點,穿過樹葉子縫,沖她眨動。和秋開始原地轉圈,整個梧桐越來越美,越來越遠,不沖亮的葉子堆得越來越薄,她眼里感到涼涼的,深海藍柔軟的天,綠奶奶的桐葉子,光就從底下,像把扇邊,扁著投下,映亮密密麻麻的葉子,蹭了葉子上邊的茸茸就黯了。和秋沒記錯,那些薄的葉一片連三五片刮到夜空的星陣,吃在夜空中。她看到星星在流動。 白天站柜臺沒人時偶然看手機,知道昨天晚上整個中國的人都在一塊塊屏幕上,打了流星字。晚上獅座開始下流星雨,接下兩天,她沒趕上。系統特意設置成倒斜的雨滴字陣,一溜一溜的敬意,和秋看了看直播回放,沒在字幕上發現成林二字。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說,在流星雨下的時候許好愿,皆靈。和秋現在沒有什么本愿,如果她正巧那晚守著屏幕,她想的不一定敢寫,想成為另一個人。 但是亦有說出來的并不能實現,有些神意總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成林其實整天低頭看手機,只要不耽誤來客要求,領導并不太介意,他看的時候挑在監控死角。那天晚上之前一周他就了解到要有獅子星的流雨,雖是大個子男性,任何方面確屬優秀,絲毫無半點再苛求心,但他在第二天的流星雨時留言央視的公屏上了一行字,沒有具體人名,他想以此避開某人,好在工作上去掉些障礙。最近由于這點小的情緒漸漸影響到他的健身,這種本能的發揮余度,讓他開始擔心接下去對能力的攻擊力。 夢今年快要四十,她并不太想最引她常記憶的幾年夏天,一個秋天。冬天的時候也多。她看見西藏,看見寧夏,漫天都是星跡。她注意瀉掉的字,據他提她才發現確實有顆星正緩速移動,他科學地稱之為勻速。然后她告訴他,哦,知道了。引起后邊一條單純情緒的哈的單字。這之后夢只找動星,隨后相繼在酒泉、西藏的山坳上方,發現許多顆成列作伴北上的星星,亮閃亮閃的,她有一刻頭歪下來,就為能欣賞全星體。所有的人就祝愿自己身體健康、家人健康、事業有成、大考順利、高考真累。等秋風過秋風后數落鴻,燈下一紙書、吟誦十四行詩,在這仲夏夜之際,她甚至見到這倆種人也在仔細觀察星海。她馬上添上句仲夏即將告別、吃了半個西瓜撐著了11點繼續原地跑,沒有回應。 和秋一轉身,自己穿上了面熟的黑紗裙,這件裙子相當熟悉,到底在哪曾見過呢?她打算好穿這件衣服的事是昨天,也可能是前一天那個下午,和秋在看成林的姿勢,她在欣賞時候她就已決定這天要這件衣服。她在欣賞。她在欣賞什么?成林,這個人。和秋畢業不久,成林比她大。她見到他后覺得這世界真還是有點意思。走吧,就算怎么想不起是哪天開始想穿這個根本不是她的裙子那也得按點到店啊。 和秋記得她還在7點5分走出家門,可到店一看表,已經是九點,她應該是走的原路,但好像見了許多樹,不應是那些普通的樓和樓挨緊的街區么。她倒見了槐樹、松柏、紅薔薇、青白紫薔薇。 她有點暈,一進門就坐到店口的膠凳子,紅的。一會兒成林出現了。他可真高,腰細得好看,身架子美啊。她一邊嘆息,她陸續默默點著自己的頭,才試著原來這上邊有個帽子,她照了照身后鏡子,發現是頂洋氣的貝雷帽。其實我是為著一人而來看看他,他會叫……他的那個名兒么?這也是昏頭了我,他怎么能和他一個樣,模樣確不如他,那他也應該姓李。我看著就像。他愛站到我身邊,不到半米距離啊,他是無聲的,無味的,靜靜的如果我那第一次忘記回頭看出門的母子,就永不知道他,有他這么個人這么個真的大個子,安靜的像只貓,一手撐墻,拉開美體,什么動靜什么氣味也沒有,連他收起動作走回也沒有。 和秋一坐竟半天。 夢醒了,眼里看到身上還蓋著單子,嚇一跳,怎么?過七點了! 夢站到家門口的21路車牌下,當她想起在烈日下低一低頭時,看到自己是裝在身火紅棉替恤里,一種美好溫情的回憶似乎靠近,但咂磨不到具體是什么,只覺得暖。那是大約十七年前事,她剛被沃爾瑪錄取,大三伏的可能是在中午,夢騎著她母親的車子路過張曼玉的巨型廣告,對笑得燦爛的人在心底問了句,啊,我21歲找到工作,不晚吧……從幾年以前好不容易走到今天午時這段時間以來的所有辛酸,里邊的淚,魚貫進雙腿,奮力向前帶來的、不久見到母親可說的,被吹上身變扁的風揉碎。這種美好與紅有關,但是它最終褪色。夢一想退掉的那件紅上衣,轉著轉著,回到二十年后沒有母親的她身上。 然后她這一路總在看樓。灰樓、白舊樓、綠樓。她隨后見到支鐵架子的廠、十二輪的大貨…… 夢在這天待滿了八小時,她有些驚嘆。 在這八個小時中,她找出此間店不少讓她愉快的物事人事。有個玩具,她看了多遍,還是不厭。一條壓彎但幽長的軌道,有倆小胖雞可按,如果你按反,它爬不上云梯,就滑不完這段光滑的賽道。這架梯子間錯在倆只小雞等待的前方。夢后來發覺是自己錯,是先推動停在道的雞,它過來踫到這個障梯,借慣性步楞步楞蹦跳一根根梯欞子,然后這股力就很大,暢通無阻。 它是借力之前先呆站一會兒。 那個叫成林的人,夢漸漸發覺他開始倦怠。她記得他是大概在五月出現,她被他宛若驚鴻的身材震過,那時候他不這樣。他整天在看手機。 以前有個人,也在這天天看他低頭在看,一直很喜歡,幾乎可稱是鑒賞。這一種似是而非的感覺夢感到在哪見過。 成林今天輪休,去了游樂場。 他做了上天飛,挑了匹白馬踏上腳撐子接著電力開動,旁邊安坐棕色高頭大馬的憂郁小男孩一路偷樂,從眼神中嫌棄他馬的矮小。最后他一人在藍色摩天輪斗中向下望著這座城,他想這時若手一抬幾乎觸云。他捕捉到一種透明色,這時廂子很靜,當他聞見陣類茶香的感覺時恍惚看到一個人的面相。他對自己在這個高度首先想起的這個人而感覺怪異,接著他發現這是再平常不過的情感。這種情感貫穿了他這一整周,如果細想,上個月亦有數十天他在想她。他有些……是懼怕,是感動,驚喜,寬慰,好像都不是。那是什么……成林癡著凝望天際,湛藍的天一個云絲沒有,這令他想昨天看的一個公號選取的宋詞:送君還是逢君處。但這是個女人,她總穿那身,沒肩的短洋裝,她有氣質,有種不打撓別人卻一直“干擾”到她身邊站得近的人的氯場,那究竟是什么?有時,我削個萍果,有一半破了個小蟲洞子,泛著微紅,我就感到似曾相識,是白天還是什么時間眼前總有這種淺豆沙色。有時,我站了一天到家累了,洗完澡坐在一個地方晾身子不經意搓了把臉,我忽然記起她坐那個暗處的空蕩蕩的凳子上時也是一個人。 總是一個人。有時我好像想完她后發覺這過去的時間已不短,陽臺放的舊席子角落插了成桿的干花藤子,那時剛剛落山的太陽早就沒了。 成林還在輪斗,正在接近白楊,飆到從高草吹上來的風夾起的土顆粒子,上升到個紅的像粉奶油糊成的屋頂子,他發現株地黃開了紫花,就不見了,他在靠近一棵向北最高的梧桐,約模到大體第三四十張葉子后看見一個烏鴉巢,那可真黑真大。然后那棵筆直白楊馬上就過來了。 一片心型葉子黏了,和另一片合成對,在這時成林口袋里那個出門看過幾遍的小存儲器啪地掉出來,他視線不離開深綠,仰著頭低手夠,最終靠感覺掖回褲兜。他眼見著那疊葉子離開。他是看著,沒半點眨眼,快得像夢,滑去之后他就有點懷疑,剛才看到沒有。他的車廂開始透明。他上升到那里的云層,底是藍的,但有層薄體。不是霧。它是澄明的。背后的樹,房頂,云彩,一覽無余地、像在地上見看慣的任何自然界該有的樣,浸在薄紗后。 浸在薄紗后頭。 和秋如果不改道,她每天應該先走一條兩向過車的街道,兩邊只在為施工而圍的綠櫖子后有行歪了幾棵的楊樹,剩下的是從她這邊小區柵欄延伸到外的一人高灌木,也沒什么香氣。每天她由這道出門,再在車中看成排的廠房,灰的、綠的、舊綠……鉆入個火車巷道口,有時有運氣會再見多年前坐過的綠皮火車,來去都沒有一聲笛。然后就到了。 夢每天如果選擇逃離那扇門,那就會再見一縱又一縱的園林。有槐樹,高可參天,太陽從婆娑小零葉中撒得勻,她好騎車,就仰頭在看,她想一直就這么樣看,但是常常記住的也不過是照下太陽來的陰影中顯成黑色的槐葉,飽看不了幾眼車子就過去,她幻想這種槐林真像某種王國里的王子,非常留戀,也很快過去。有槐樹,一棵接下一棵下去,都在招手,從漫天、從她原先該應擁有的那個世界,美好地招手。有棵紅樹,孤零零的站在個高速出城口,它長得圓,有很多濃得如酒的葉子,每次騎在下頭心底照應一下,哦你啊,接著就過去。有槐樹,回去的時候,來的時候,有槐樹。 都是槐樹。 成林以前休息是在周四,但在這天他從不上小孩子去的地方。然后他會看存在盤里一周中沒空觀賞的電影。這些電影大多是網飛制作的歷年外國疑案回溯。他往往沉浸在一兩個或悲傷或生疑問的面孔上得到一種安穩,因為他失去了母親。并從那以后不對任何自然界里使自然人產生感動的事多一點同情,這或許不是恨,但更不是殲忍,決也不會是變態。沒有人在不經歷此種事前能理解他這種感情的份量。 2021年8月12還是10號,反正出不了這期間,宇宙中下了場英仙座流星雨,但是事后他三人卻都錯記成獅子座。這無關大礙,英仙和金獅都曾在不同年份里下過流星雨。這種雨和大自然里用肉眼能見到的雨絕然有異。不論雨后還是雨后之前的時間,眼里看見的是偏黃的凈水滴子,高倍望遠鏡中它是不動的,固體。所有的星有大的,更多是小的,紛紛雜雜,離離駁駁,誰也不挨誰,誰也其實不遠,但不被知道,亮著、高著。有時,偶爾一兩三顆星星想動身子了,就游走,就離開,看著就像是流動雨,但這時人不記得悲傷,反認幸運,在其下說上其實根本不可能實現的事實。 在這同一天,和秋在嗶哩嗶哩站見到英仙流雨。 夢在央視站點分別去西藏、去寧夏、去西川看金獅流雨。 成林呢,有時他寫下點東西,怕被遺忘,有些寫完就有點后悔,抓住的好像也并沒像他希望誠心記下來怕自己忘了的。有時他在削個水蜜桃,刮剜到半點淌糖的凹陷時偶然瞥了亮著的電腦,在關小的頁面中,他仍看見一句祝福,有的人見一面,誤終生。他手中果就斜了斜,亐他身長手大,果子來到手邊也就止住,他心意外震了震。 許多年過去,那個玩具依然暢銷。說是廠家曾有人提議可改一改兩只小鴨等待的事,不指時間,而是個數。有的說換三位,有的想想后還是覺得原來兩只來得巧,因為人一旦多,那就不會有思考更改的結局,就不會呈現給大眾呆傻可愛的表象,世間不都是喜歡傻下去點的人么?或是只有傻了人才能活下去。所以仍就讓原物原樣生產。 但是在眾多銷售它的門店中,仍繼續有三人,一見兩只小鴨在等待,一直等待而沒有任何面相,還是覺得是有點遺憾勁,于是就往下可以讓他或她幻想順利滑下去的梯子瞧,一瞧就是老久。 作者:李萌憶李承林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2746107 出处:bilibili